|
|
|
姜渝生 成功大學都市計畫系教授
《草原雜誌》是西格瑪社友進入社會的第一項「作品」,文訊雜誌第240期第 96-106頁有兩篇相當詳細的報導,作者姜渝生已取得該雜誌同意,可以把這兩篇文章放到西格瑪網頁上。 劉定泮 11/7/2005 台北縣新莊 |
|||
|
清新、園地開放、充滿理想性的《草原》雜誌,是台灣第一本明確標榜本土文學藝術的雜誌,從創辦起始至殞落雖僅一年,卻代表著一群年輕人執著追求文學夢想的紀錄。 一封來自草原的邀請 民國56年6月,台灣各地有不少知名作家,藝術家,年輕的文藝耕耘者,以及大專院校學生刊物收到了一封《草原雜誌》的邀稿函,具名的是兩位從未聽過的名字:林蒼生、姜渝生,卡片係以120磅銅版紙套色精印,其文曰:
這封邀稿函在當時的文藝界曾引起相當的注意與好奇,一方面是因為設計精美,而且大量寄發的邀稿函,在當時是一項創舉,而邀稿函的內容明確的宣示了一本新的文學藝術雜誌的精神──「要愛泥土,生命以及陽光」,在當時現代主義及前衛藝術正引領風潮的時代,也自然格外的會覺得有所不同。 《草原》雜誌雙月刊創刊號於民國56年11月 15日問世,其創刊辭中更進一步的強調了它的宗旨與方向:「我們認為藝術是健康的心智活動,它肯定而且向上,在習見生活裡面而不在觀念之中。文學藝術像草木,滋長在泥土上,面向空氣與陽光。」這份清新,園地開放,又似乎充滿理想性的雜誌,加上資金似乎相當雄厚,所以出刊後頗受到文藝界的重視,可惜只出版了三期就停刊了,前後不到一年。從台灣文學雜誌發展史的角度來看早夭的《草原》,當然只是眾多前仆後繼的嘗試者之一而已,並不會有什麼重要的貢獻或影響,但有幾個特別的地方還值得一提。第一,台灣民國50及60年代的文學雜誌諸如 《筆匯》,《創世紀》,《現代文學》,《文學季刊》等,開始時多多少少都是同仁雜誌的性質,《草原》雜誌則只在提供園地,而且還企圖提供稿費。其次,它在創刊號就明確的宣示了第一年各期的主題,出刊了的三期都係按照原定的主題沒有改變。第三,它應該是台灣第一本明確的標榜本土文學藝術的雜誌,反對盲目的西方橫向移植。第四,這本雜誌在版面設計及內容策畫上也多有新意,諸如第一期有關現代詩的兩個專輯:以簡短的訪談方式表達對現代詩看法的「詩給了我們什麼?」以及詩人及文學藝術家從不同角度評論的「如何將詩帶進我們的心靈?」似乎就多少啟發了民國60年創刊的《龍族詩刊》的論詩專輯。 由於《草原》雜誌一開始就意在提供園地,做為園丁而非同仁雜誌,所以文藝界在當時並不很清楚是那些人在辦這本雙月刊,只知道是成大剛畢業的幾個年輕學生;《草原》停刊之後自然就更消聲匿跡了。因此今年4月底筆者在學校接到《文訊》封總編輯的來電時,相當覺得錯愕,事隔將近四十年居然還有人記得這份只出版了三期的刊物,而兩天後封總編的email也提到了一通電話居然找到了三十八年前《草原》主編的興奮。未加思索答應了寫一點記錄「草原」故事的文字,卻使我一下子陷入了回憶的深淵中不克自拔,多少陳年舊事一幕幕的重新浮現在眼前,看著一封封塵封的舊信及文件,心中免不了充滿了許多傷感,無可奈何與追悔。中間曾試圖商請封總編同意改以第三人稱方式簡述以交差了事未果,只好勉力的完成此文,就姑且作為60年代的年輕人追求理想的一段故事紀錄吧。 從火星社說起 故事的源頭得從民國52年成大所成立的一個學生社團「火星社」說起,52年2月成大電機系一年級學生劉定泮與林蒼生等人,發起成立「火星社」,其宗旨為「喚起青年人真摯的熱情,促進年輕人對知識的探求,培養獨立自由的思想」,強調「自動,熱情,沒有拘束;誠懇,友愛,互助合作」的火星精神。在沉寂的工學院校圖中,招收會員的海報極為突出,吸引了不少成大學生的加入,其中包括建築系二年級的姜渝生•王小娥。 火星社於民國54年10月改名為「西格瑪」社,西格瑪即希臘文「Σ」的譯音,其意義指文學,藝術,哲學與科學的整合。西格瑪社在那個年代的台灣是相當著名的學生社團,成大喜歡文藝及思想的學生幾乎都曾經參加過西格瑪社,可以說人才濟濟,鄭南榕先生在55年度上學期即曾擔任過社長。當年台北市的耕莘文教苑是年輕藝文界,思想界發表議論最著名的場所(呂副總統當年留學回國時即曾在耕莘文教苑倡導女性主義),西格瑪社的成員當時也常常北上到耕莘文教苑去「大放厥辭」。西格瑪社在成大一直維持到幾年前才結束,歷年代有才人出,會員們的向心力很強•彼此感情很好,到現在都還常聚會。 《草原》雜誌的誕生與西格瑪社有直接的關係,上述《草原》雜誌的許多理念可以說就是來自於西格瑪精神。當時西格瑪諸君都相當,不安於室」,不太滿意工學院的刻板生活,差不多每半個月左右會有正式或非正式的活動,文學、藝術,音樂或思想性的。生性害羞的我記得還曾大膽的在大禮堂公開演講「現階段中國新詩之動向與未來」,其結果不理想可想而知。最典型的火星社(之後的西格瑪社)活動是七、八人至十一,二人不等,找個寫意的地方相聚在一起,沒有什麼特定主題但非常認真的談一些人生看法及理想,常常到天亮還捨不得停止•大學最後一個學期時,大概是不甘心畢業之後從事工程師的工作,也可能捨不得西格瑪生活的即將結束,蒼生、定泮、小娥等人逐漸興起了投身文化事業的念頭。民國55年3月西格瑪出版了唯一一次的鉛印社刊,更啟動了蒼生的決心,55年3月22日寫信給當時在桃園服兵役的筆者,表示決定不出國了,要以文化事業為志業,首先從辦一份真正高水準的刊物開始,然後辦出版社、文藝沙龍、乃至電影等等,初期資本額二十萬元,需要時可以再增加,希望我能大力協助,並尋找好的人才共同奮鬥。 編織龐大的文化事業夢想 當時蒼生父母親同意提供總額度五十萬元給他創辦文化事業是非常難得的事情,這個決定應該與蒼生的母親有密切的關係。蒼生給小娥的信中曾寫到:「我有一個世界上最好、最美的母親,我所有詩性都來自母親的詩細胞;媽成詩一首、一定先給我看,我寫多少,也一定叫媽知道」。 接到蒼生來信後,我最先連繫的是時在台大中文系的中學同學黃啟方,中學時筆友周浩正,以及經由浩正而成為筆友的郭承豐等三人。浩正當時係投筆從戎服役於澎湖,非常熱心且持續不斷的提供許多主意,同時介紹了許多年輕朋友。承豐當時在國華廣告公司任職,為國華最傑出的廣告設計師,而李南衡則為國華當時最有才華的AE,郭李二人正商議要離開國華自行創業,二人都為蒼生的熱情所感動,郭的藝專同學林安潮也希望加入,這些年輕人便開始了一個龐大的文化事業之夢想編織。 55年3月至6月底這一段期間,一方面蒼生,定泮、小娥等在成大開始構想許多未來文化事業的內容及做法,資料顯示55年4月24日曾開過「西格瑪文化事業公司」的第一次籌備會議;一方面則由我在桃園軍中草擬文化事業的企畫書。透過信件往來的交換意見,4月底提出了初步企畫書確定了大方針:文化事業的宗旨是「使所有的年輕人體認自我,明白責任,踏實的努力於所願。不受壓力」,先從藝術做起,而且「真正的藝術一定要是帶血肉的,建立於生活之體認上的,決不是建立於名詞之上,建立於空想之上、建立於不自覺之上的。藝術家一定要有責任,增進整個社會的心靈世界。」雜誌的對象先以大學生及大學畢業生之年輕人為主,以及中學生。 接著在5月中旬提出了廣東西美術事業公司」籌備報告,文化事業的名稱決定為「東西」,事業的範疇除了文學雜誌之外,還包括藝術雜誌,青年雜誌,婦女雜誌,出版社、廣告設計公司,文藝沙龍、畫廊,劇團,電影公司等等。並決定第一步以文學雜誌為主。而在籌備雜誌之同時,擬先推出廣告設計公司,希望以後者的盈餘挹注雜誌及出版事業,有助於整個文化事業的永續發展。以美術事業而非文化事業為名是因為蒼生對當時政治環境的顧慮,而先推出廣告設計公司則與郭李等人之加入有關。5月下旬成大畢業期考一結束,蒼生與定泮即搭乘平快夜車北上,我中途從桃園上車會合,小娥則於第二天考完北上,與承豐、南衡等南北大會師。還記得在興高采烈的談了許多未來的想法之後,走過台北街頭中廣公司的公車站牌時,這一群不知天高地厚的年輕人當中有人曾興奮的喊出來,將來「東西」也要能成為公車站牌的豪語與憧憬。 「東西美術事業公司」正式的籌備工作於55年7月後展開,很不幸的蒼生與定泮都分發在澎湖服兵役,所以實際的推動只能由剛退伍的筆者負責,先係暫在亞洲傳播公司成立工作室,10月時搬到仁愛路二段。而號召年輕朋友的參與也在浩正與蒼生、定泮等的熱情下如滾雪球般擴大,有興趣加入或提供協助與建議者越來越多。其後由於姜,林主要的興趣在文學,而郭,李主要的興趣在設計,不易調和的分歧終於導致了兩股力量的分道揚鑣,承豐等人在56年1月另行創辦了《設計家雜誌》,而其他人則搬到台北市金門街正式開始了文學藝術雜誌的籌備工作,並於3月間命名為「草原」。事實上,這並不是一開始就決定的名字,開始時曾經想過的刊物名稱記得還有「怒江」,「太陽」、「創意」、「東西」、「文學人」等等。 《草原》萌發過程 除了承豐,南衡等人之外,當時還有一股力量也因理念不同很可惜未能整合在一起,即谷文瑞,何文振,林添貴,周天瑞等八位很有才氣的建中同學,因為谷文瑞在成大參加了西格瑪社的關係而認識。《草原》籌備期間文瑞與文振曾提出了一份廣文學人季刊,的創辦計畫,並且草擬了頭兩期的內容--專輯介紹田納西威廉斯及海明威,希望蒼生可以支持,由於與《草原》的本土化理念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最後並沒有同意,文瑞與文振也就未能加入到《草原》來,只有王津平,林添貴與鄭永富三位後來一直在《草原》幫忙。此外,當時還連絡過非常多大專院校年輕人及刊物編輯,談過許多合作的構想,可惜名字都不太記得了。 由於東西廣告設計公司籌備期間龐大的人事費用,加上承豐所設計配上蒼生等所寫有趣小句子的精美聖誕卡叫好但不叫座,虧損甚大,資料顯示57年2月時蒼生父母所投資的第一期款(二十萬元)已經只剩下了八萬元。所以蒼生從澎湖來信決定,除了《草原》雜誌之外,其他的包括出版社,文藝沙龍,以及咖啡屋等的籌畫工作暫時都停止,等其退伍後第二期款有著落後再繼續。為了有一些收入,但希望只能勞身不能勞心,以免影響《草原》的籌備工作,記得當時還曾認真的談過要不要開一間冰店的事情。 那一段時間蒼生,定泮、浩正都遠在澎湖,當時的環境交通不便,又都在軍中,對 《草原》籌備過程的許多理念的分歧,人力的不能整合,加上財務的壓力,種種焦慮,關心、但又使不上力的無奈,充分的顯示在密集來往的書信中。在大學畢業時,蒼生曾意氣風發的寫了紀念大學生活的一首長詩《無人島》,其中有這樣的句子:「我欲以雨露灌溉/以星輝/栽成滿地花朵/我要完美的/圃成永恆的生機/或者 就以靜默等待/等待如是淨土的再造」。這半年的時間,《草原》的重擔,使他的來信中出現了「我忽然想起了愛情,請不要告訴我,這就是疲倦的象徵」、「我於孤獨之中噬啃著孤獨的滋味」、「做下去,做下去,只靠勇氣支持,沒有其他……」這些現在重看時還覺得心酸的句子來。 56年7月林、劉二人退伍搬入了金門街,《草原》創刊號的籌備已大致成形。為節省開支,定泮白天在台灣通訊上班、小娥在太平洋電線電纜上班,晚上到《草原》,蒼生9月時白天亦到台灣通訊上班,編輯的工作主要由我專職在負責。除了蒼生等之外,還有津平、添貴、永富及黃國蓀等年輕朋友義務幫忙,施叔青、黃啟方、章景明也提供了不少協助,「如何將詩帶進我們的心靈」特輯中,包括余光中、顏元叔先生的多篇大作大多是他們幾位協助邀稿的,而陳映真、黃春明、七等生、李鍚奇等先生則給予了許多鼓勵及建議。 多位文壇前輩的提攜與指導
記得第l期有關現代詩之專訪中「期待,跳躍,墜落,嗵!」的四張有趣的小貓照片是蒼生惡作劇的調侃,蒼生給我照片時那純真的,捉弄的笑容我還記得很清楚。詩之專訪中的手繪小插圖,係取自施叔青當時在看從圖書館借來的一本西文書,非常感謝她將早期的重要作品《約伯的末裔》給了尚在籌備中的《草原》,記得當時我們還曾用心的討論過書中主角江榮所敘述的故事情節。非常感謝黃春明先生將力作《癬》給了《草原》,記得當時還曾囑咐我不要用黃春明三個字,替他另取個筆名發表,我擅自作主沒有徵詢他的同意就用了他寫雜文的筆名邱文祺;記得黃春明還曾用心的一頁一頁翻閱了第2期,指正在編排上可以改進的地方。 《草原》雜誌創刊號在11月15日問世,11月 12日在金門街舉辦了相當盛大的創刊茶會,有不少知名作家及年輕朋友參與,確定記得的有林海音,余光中,季季,管管,梅新等人,汪其楣教授最近偶然說起她當時在台大也曾參加,記得余光中先生等曾致辭給予鼓勵。創刊號出來後記得曾陸續收到不少讀者的來函打氣,至今還清楚記得高信彊先生寫在明信片上的「草原萬歲!」四個大字。
第2期的編輯工作又加入了定泮中學同學、時在台大外文系的傅運籌,以及文化學院新聞系的關甲申的幫忙,傅關二人主要協助對外的訪問稿及邀稿,民俗文學的訪問專輯主要就是運籌與甲申負責的,甲申亦同時負責對外業務,當時還有朱龍勳及張錦焜兩位年輕朋友時常來幫忙•非常感謝司馬中原先生等九位知名作家學者接受我們的訪問,也特別要感謝丘延亮「現階段民歌工作的總報告」的詳細記錄。《草原》第三期的主題為「空間藝術」,所以又商請筆者中學時結識的筆友畫家顫重光來協助,民間藝術訪問的專輯即是由重光,甲申及丘延亮先生三位負責的。而程抱一先生遠從法國寄來與亞丁談詩的大作當時也使我們興奮很久。 《草原》第2期於57年1月出刊後,為節省房租,從金門街搬到了羅斯福路巷內,我也搬到了永和•第3期於57年6月出刊,延遲了三個月,雜誌的最後一頁曾預告了第4期,並宣示一期一期辦下去的決心,但第4期並未能如願推出•現在回憶起來,無法繼續辦下去的主要原因可歸納為三點:第一是錢的問題,第3期出刊後,蒼生父母所提供的第一期款已差不多用完了,記得蒼生還不時從日本寄來省下的生活費;第二是人的問題,蒼生赴日後不久,我也在57年7月到經建會工作,之後運籌又赴美留學,事實上已經沒有人可以負責編輯的工作了;除此之外,亦與陳映真於5月被捕事件多少有關,據甲申回憶,當時警總曾派人至「草原」訊問陳映真先生與「草原」的關係,這對單純的年輕人而言,多少也產生了一些影響。 憶當年,多傷感 以《草原》雜誌的資金,卻只能維持三期而已,必然是犯了不少的錯誤,最該負責任的當然是受蒼生重託的主編了。在籌辦文化事業初期所走的岔路,耗去了太多的資源,以至於原來所企圖的許多想法(蒼生的出版計畫,定泮的半月刊青年雜誌、小娥的文藝沙龍……)還沒有開始嘗試就都夭折了。 而在《草原》雜誌的編輯中,執意要做到最好卻又力不從心,在準備第2期時就一直為之苦惱著。第1期之詩論的結尾,陳映真先生以許南村的筆名曾寫道:「我深深地相信/通過詩人本身的藝術良知/通過基於把台灣的新文藝帶向一個更高的次元的共同意願/通過不斷學習的熱意/通過文學範圍內務分野的文學工作者謙虛的合作/不僅是詩,連帶地是小說、散文等等/都會有一個更豐收的季節/讓我們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吧!」這些話深深的感動了當時的蒼生與我,不自量力的、稚氣的覺得也仿彿參與在一個即將豐收的期待與耕耘之中了。但當時的大環境對這樣的認知並沒有普遍的共識,具有這樣使命慼的作家也不多,所以要在短短的時間內收集足夠的好作品付梓,對不是同仁雜誌的草原來說,就有如千斤重擔般的壓力。因此,在第3期「空間藝術與我」的專訪中,就借著陸文其的話深深自賣著:「我覺得這種黴文沒有多大意思,重要的是拿出作品來。很佩服貴刊的用心,以及所提出的r文學藝術像草木,滋長在泥土上,面向空氣與陽光。」希望草原拿出這種作品來,拿不出來多埋頭苦幹,不要空討論」,這樣的自責可能是最終放棄《草原》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這兩個月多來,由泛黃的舊資料,同時走訪了好幾位多年不見的老友,逐漸重溫了一遍當年的情事。似乎像是流水帳一樣的記錄著,內心事實上是澎湃不已,想起了一些充滿稚氣的堅持,無力兌現的承諾,以及對於明知的人生囿限的無力掙脫,而終至於選擇了不負責任的離開,深深覺得汗顏與不安,及至讀到了寫著「從前,我們有過美麗的微笑:從前,我們的靈魂曾手牽著手:我們,曾步調一致的走過路!」的一封舊信時,眼淚就再也忍不住的流了下來……。 <本篇完> |
|||
|
|
|||
|
《草原》概述 ◆許芳儒 中央大學中文所碩士生 由一群成大工學院學生創辦的《草原》雜誌,雖僅發行三期即告停刊,但其特殊的編排和設計,充滿民族意識的宣告與鼓舞,具體展現出文藝新血的豪氣與理想。 源於傳統、傲視現代 經歷了西化潮流日趨衰頹的1960年代後期,台灣社會進入了以民族認同為主題的回歸時期:而由成大工學院學生創辦,並提出「緣於傳統•傲視現代」八個字為口號的《草原》雜誌,便是在此風潮下的一席文藝見證。 《草原》雜誌創刊於民國56年11月15日,以雙月刊的形式發行,其內容主要是文學藝術的論述、批評,詩,散文,小說,戲劇、繪畫,木刻等文藝作品;發行人是林蒼生(兼任社長),主編則是姜渝生,由當時位於台北市金門街的草原雜誌社出版。雖然前後僅僅發行了三期即告停刊,但其特殊的編排和印製,充滿民族意識的宣告與鼓舞,卻必然在台灣文藝雜誌史上留下不可磨滅的痕跡。 在《草原》創刊號的刊頭語中寫道:
此番擺脫歷史包袱,以今時今日為原點的言論,便已具體展現出文藝新血的豪氣與理想•事實上,在第一期中,《草原》已然提出了第一年的內容藍圖。在第一卷中,將分為六期,逐期討論不同的主題,分別是「詩」、「民俗文學」、「空間藝術」、「短篇小說」、「文藝批評」、以及「作品發表」。 詩為主,內容包羅萬象 總頁數達123頁的創刊號,內容包含了訪談兩篇,散文九篇、形式特殊的散文詩兩篇、小說兩篇(其一為翻譯小說),書介兩篇,共計十七篇。 由余光中所發表的《在中國的土壤上》’無疑是極具份量的第一砲,針對民族自信心喪失•對西方思潮囫圃吞棗,導致現代詩創作的虛無,晦澀等現象,提出了擲地有聲的批判,並且絲毫不損及文學的美慼,他說:「為了服西方新上市的特效藥,此地的作者先學會了西方人的流行性感冒。」在編排上,《草原》匠心獨具的將余光中這詩一般的句子以藝術書法體突顯出來,將其剛柔並濟的特色表露無遺。 此外,李篤恭《現代詩底問題》、辛鬱《剖析商禽詩作鴿子兼論當前詩壇》,大荒《談詩的晦澀》,蘇淺《將詩帶進我們的心靈》,林煥彰《讓詩駐進我們的心靈》,許南村《期待一個豐收的季節》這六篇文章亦將重點放在批判西化帶來的晦澀上,與余光中的立論相互呼應。《草原》以這麼大的篇幅處理這個「去西化」的主題,更顯示出其改革的立場。 而在「詩」的主題之下,管管、顏元叔各自發表了《梯子》、《乾澀的思想在乾澀的季節》這兩首形式特殊的散文詩,形成了「以詩論詩」的特殊風貌。 而由鄭永富、林嵐所負責的訪談單元《詩給了我們什麼》,則是以一般社會大眾為取樣對象,選出二十篇來自不同年齡層,不同職業的調查結果,呈現出各階層人士對廣詩,的看法。而專訪方面,則是女作家林文月暢談她對詩的一些思考。 除此之外,創刊號的內容還包括了七等生《作冬來花園》的散文作品、施叔青的小說《約伯的末裔》,翻譯自芥川龍之介的小說《報恩記》,古渡的書信體散文《背景──寫給我們的朋友們》,以及孫旗關於歐普藝術背景與發展的專業書介《視覺反應──威廉•塞特茲原著、黃奇銘譯介的〔北歐神話〕》。 由孫旗、余光中、林文月,以至七等生、施叔青,這樣的作家陣容、作品數量看來,說該刊「包羅萬象,十分豐富」可是一點也不為過。雜誌的最末頁《起步的時候》,則是編者們的徵稿啟事。以詩為主體的堅持、對雜誌內容廣度的包容,都可由此看出端倪:
第2期的頁數增至149頁,發行人仍是林蒼生先生,社長則由關甲申新任,主編為姜渝生,傅運籌,當時雜誌社已遷至羅斯福路。不過奇怪的是,第二期雜誌上完全沒有標記出版時間,因此是否準時發刊便不得而知了。 這一期的內容也是三期之中最多元的。不論是議論性的學術論文•散文、小說,詩,戲劇,訪談,西方文學譯介,漫畫各方面,均涵括在其中,總計有二十篇作品。 小說類有邱文祺(黃春明)的《癬》,漫畫類有巫華果的《草原漫畫選》各一篇。 散文類則有王秋實的《給武雄的信》•黃美序的《雜慼隨錄》,李篤恭的《假日》,朱介凡的《秋暉隨筆》,管管的《是鳥是魚是火是煙是吾們》,共計五篇。 議論文部分則有強調人文精神,藝術價值的議論文:向邇的《當代作家的使命》,李錫奇的《現代藝術再開始》,彭紀政的《但丁神曲與吳承恩西遊記比較》,黃士選的《中國神話》四篇;以及介紹西方文學的雜文,如顏元叔的《休謨與古典主義--現代文藝思潮的開端》,何欣的《美國小說家波爾狄》,傅運籌的《埃及神話》等三篇。 在詩的部分,除了辛鬱的劇詩試作《永遠是二對二》之外,第二期增加了一個新的專欄「草原詩草」,主張「一首詩應該如一株草,自泥土中滋長出來」,收錄了林煥彰的 《中國中國》,張健的《山便是你》,林安助的 《午後的禮拜》等三首詩。 至於第二期的主題「民俗文學創,則以57頁的篇幅佔了全刊三分之一強。主打訪談稿《談民俗文學》,是司馬中原、朱介凡、呂訴上、吳瀛濤、林海音、俞大綱、魏子雲、蘇雪林、顧獻樑等九位作家學者的訪談紀錄,另外還有丘延亮的《現階段民歌工作之總報告(1966 - 1967)》,都是極珍貴的參考資料。 綜觀《草原》在這一期的選文,多偏向專業的學術路線,純文學的創作反而少了。 也許是意識到這樣的情況,「徵稿啟事」在本期中有了全新的聲明:
願為原上草,萎落又再生 第3期的《草原》雜誌似乎已然顯現出經濟窘迫的壓力了,除了其發行的時間(57年6月15日)足足比原定的3月15日晚了三個月之外:在篇幅上,也驟降為八十四頁。雖然在雜誌末頁中,還附加了延遲發行的道歉啟事,並且希望讀者能夠繼續期待,但在這之後的第四期,卻再也沒有出現了。 而這一期在內容上,遠遠比不上前兩期的精采程度。以「空間藝術」為主題的專文,僅有林徽音的《中國建築藝術》,顧重光,丘延亮的《民間藝術訪問》兩篇,即使加進繪畫藝術的部分,如莊世和的《談超現實主義的繪畫》,余弘毅的《從民族性的比較看性在東西繪畫中》,也不過只有篇幅不長的四篇。 而如此一來,其他內容便只剩下程抱的西方文學介紹《與亞丁談詩--談藍波》•朱介凡的雜文《窗、橋,塔》,張範雄的譯介《愛斯基摩神話》,以及黃美序的雜文《談紅樓夢》四篇。 第三期雖在內容及份量上都稍嫌薄弱,但其美術設計,卻仍維持住一定的水準。而這也是談該刊物不可不提及的一部分。 除了在選文上偏向學術性、批判性,作者群多為名家這兩大特色之外,資料不多的《草原》最引人注目的,還是它獨樹一格的版面設計•首先,前所未見的「17.5X23cm」大小開本,即充分顯示出它的「特殊性」;而多以國劇臉譜,龍鳳圖騰作為內頁精緻的小插圖,亦成為其特色之一。 此外,《草原》對於書法字體,以及套色印刷的運用,也是一絕,從封面、目錄、內文,甚至連英文字都大量使用書法字體,這想必是表現主義的趨勢產物。而「源於傳統」的信念,也在這種設計下得到了新的詮釋。 但願這樣的勇氣與創意,連帶辦雜誌的那股「傻勁」,能如同真正的原上草,即使已然萎落了,只要春風一來,就能以不同的形式新生。 註釋 1.《草原》創刊號,1967年11月,封底。 2.《草原》第2期,出版時間不詳,封底。 |
|||
|
第97頁右上圖說明:《草原》廣發的精美邀稿函,正當時文藝界曾引起相當的注意與好奇。(姜渝生提供,以下同)
第99頁右上圖說明:《草原》創辦人林蒼生(右二)和主編姜渝生(右三),攝於民國57年2月《草原》舉辦活動時。
第101頁右上圖說明:小說家施叔青的《約伯的末裔》、黃春明的《癬》均在《草原》上刊載。(文訊雜誌資料室)
第104頁右上圖說明:充滿民族意識的《草原》雜誌。
|
|||
|
|
|||
|
|
|||
|
|
|||
|
|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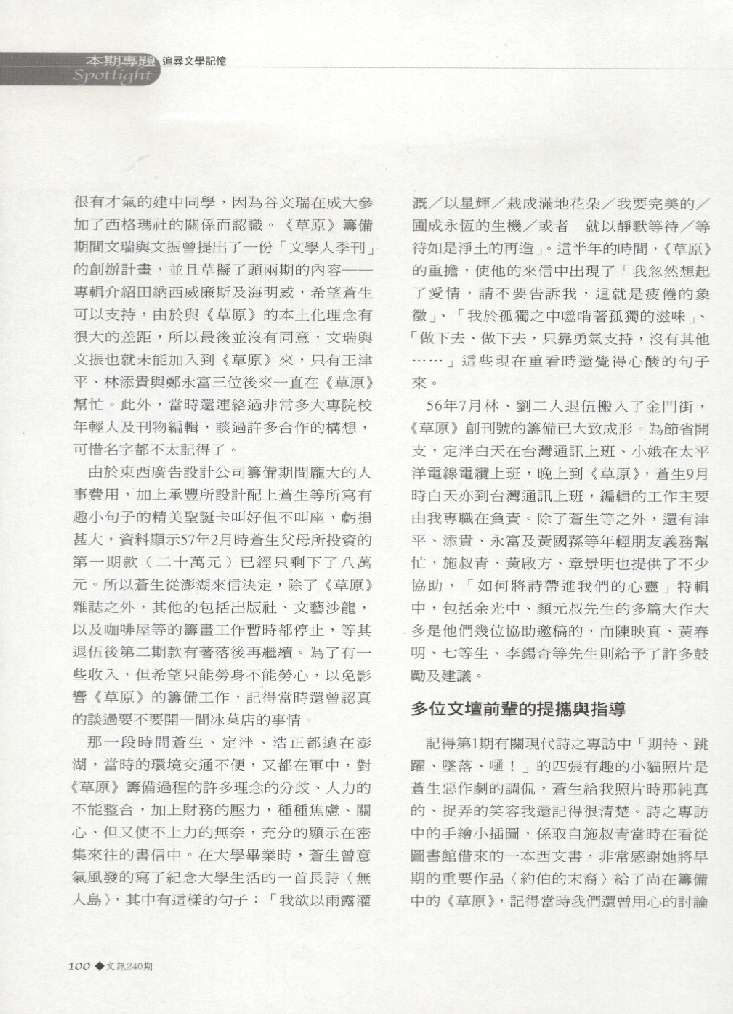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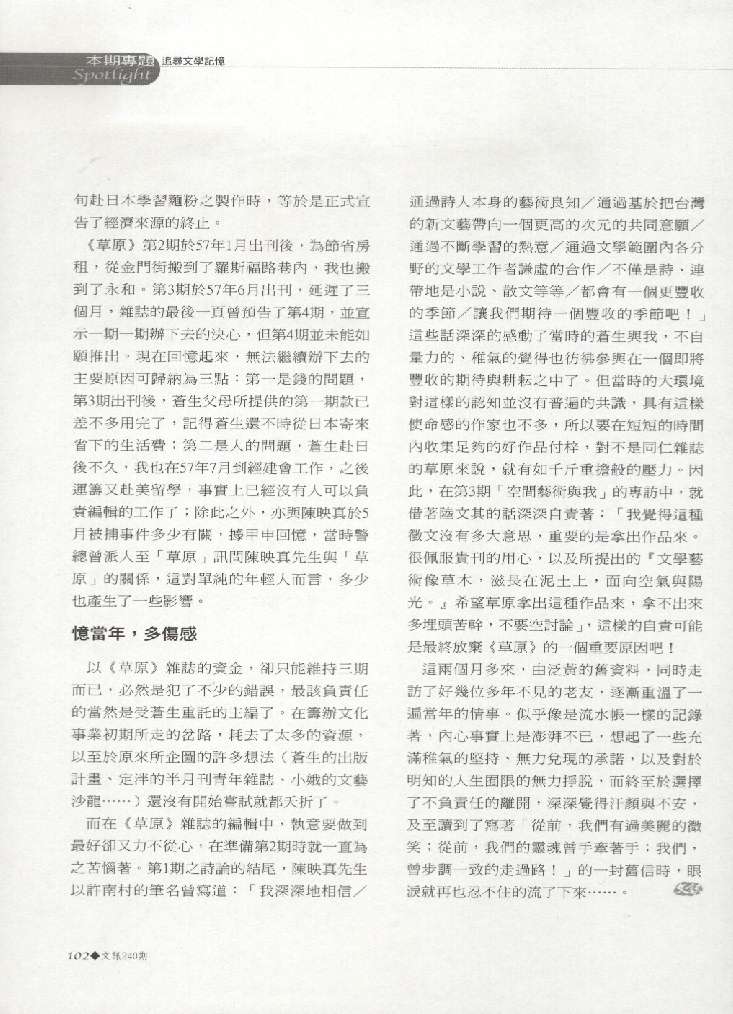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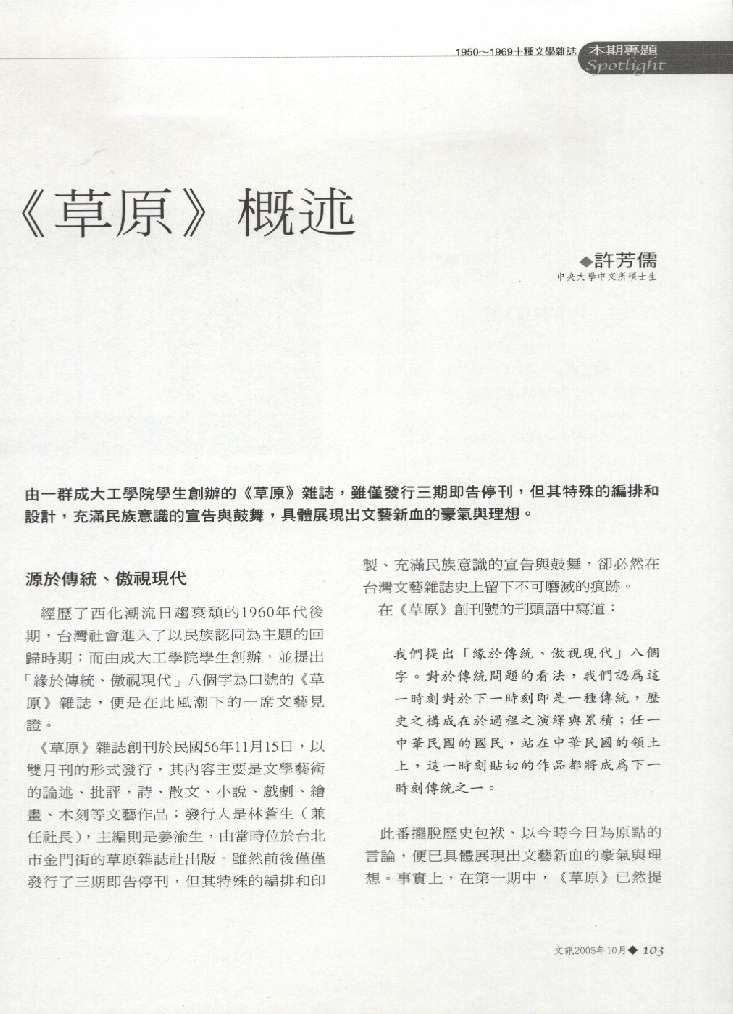 |
|||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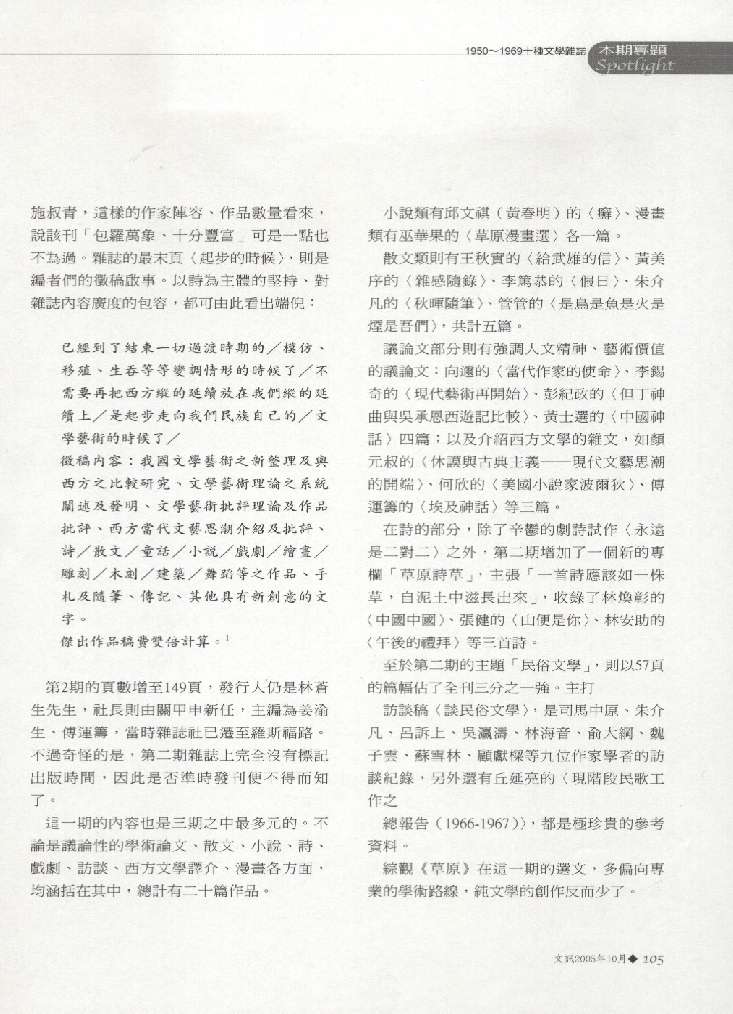 |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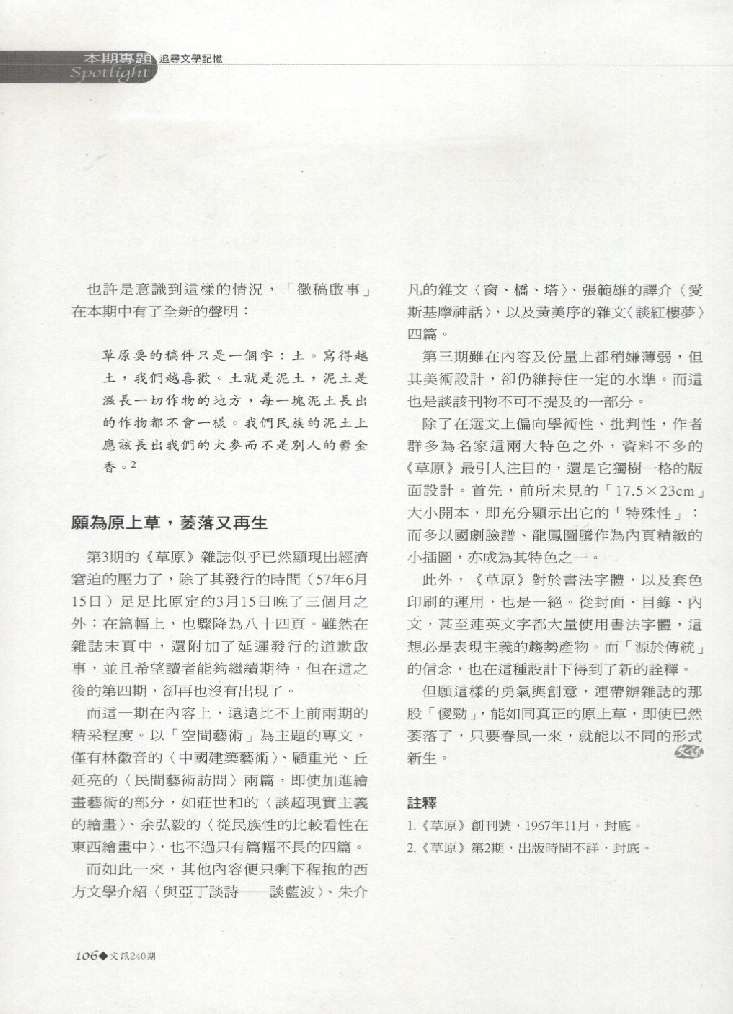 |